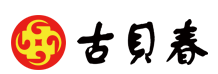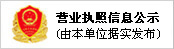生于五十年代
新闻分类:墨香酒韵 来源:古贝春报编辑部 发布日期:2015-05-04
我和丈夫的父母都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
父亲那代的男人甭管酒量大小,几乎都爱饮酒。至今父亲都保留着饭前先饮酒的习惯,每天午饭晚饭前两顿酒,几乎雷打不动。酒不挑拣,就当地产的古贝春酒,酒肴不挑拣,抓把自家种的花生,或是搓洗个苹果,有时也把上顿的剩菜稍稍一热,转眼间三两烧酒就能美美饮下。
父亲那代人把喝酒比吃饭看得重要,老父亲甭管到哪儿,不挑拣饭食的好坏,只要能让他把酒喝好。若是家里来客,老父亲更是会把自己从来不舍得喝的酒与别人同享。父亲酒量一般,喝酒时从不藏着掖着,倒是客人还未多,自己先有几分醉了。
父亲醉后,母亲只是看其脸色,若见高兴,才敢唠叨几句:
“都这么大岁数了,少喝点不行吗?”
这往往是母亲对于父亲醉酒的嗔怪之语,每次醉酒后母亲都会絮叨,但却从未真正阻拦过什么,照样会给父亲杯子里倒满水,送到他手里。
父亲几乎不会搭理,且把这絮叨的话随着水喝下了,若真被母亲絮叨烦了,随后便是一通训斥。
“要是都不喝酒,你闺女的酒都卖给谁去?”
权当这是父亲的醉话,但母亲对于父亲有种特别的敬畏,那种敬畏或许源于父亲暴躁的“大男子主义”。
不单单是父亲母亲,我见惯了他们那代男人对妇女的傲慢轻视、吹胡子瞪眼,见多了母亲她们的忍气吞声、唯唯诺诺。
母亲那代女人大多不识字,但却对封建礼教很是恪守。母亲不懂何为“三从四德”,但她那辈人一生的行为却被这封建的礼教禁锢着。母亲没上过学,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年幼的小姨无人照看,姥爷便阻止了母亲的求学之路。姥姥是裹足的小脚,干不了力气活,12岁的母亲便开始摇摇歪歪的去湿滑的井边担水做饭。农闲时,她便要捉针引线,为一大家人帮衬着缝缝补补。18岁那年,就因为姥爷曾在集市上跟父亲匆匆见过一面,便一门心思把母亲嫁到了父亲那个破烂不堪的家庭。19岁那年开始,母亲便陆陆续续地生下我们姐弟几个。记忆中的母亲总是忙忙碌碌的,我们几个姐弟年龄挨得很近,小时候的母亲因为照顾孩子没坐下吃过一顿囫囵饭。
印象中,父亲从没有照看过我们,也依稀记得父亲和老祖母吃完饭后,把饭碗一搁,会盘起腿来聊天,对一切不管不问。母亲匆匆吃完饭后,还得着急忙慌地去刷洗碗筷。
母亲似乎没怨恨过什么,她习惯劳动,习惯每天为别人活着,习惯了在家为父母活,出嫁后为丈夫孩子活着。
我是那批生于五十年代的人的孩子,在娘胎里就没得过口福,更没得过休息,母亲很喜欢吃煮熟的鸡蛋,生了几个孩子,坐过几个月子,就这鸡蛋,根本没吃够过。
“那时候别人家也不富裕,鸡蛋也送不了几个,煮熟了,孩子们都眼巴巴地看着,哪舍得自己吃?”
直到现在,每次回娘家,我都会给母亲买鸡蛋。自己当了母亲,才能体会母亲那话的深意,懂得了那辈女人的不易。
当我生孩子后,有一次母亲看到我招呼婆婆给孩子洗尿布的时候,母亲背后责怪了我。
生了我们姐弟几个,母亲几乎没休息过一天,也没让奶奶和姥姥洗过一次尿布。
倒是母亲常跟我絮叨,父亲血压不好,还常爱喝醉酒,自己也劝不住他,父亲老了,暴躁的脾气一点没变。
“这喝酒的习惯都是你把他惯的,换做是我,我可不依他,不跟他闹翻天才怪。”我说。
转过头再看母亲,母亲低头像是喃喃自语,显然是怪我有时候对丈夫说话太过刻薄。
我是得意于在母亲面前炫耀我整治丈夫“陋习”的招数的,跟父亲相比,丈夫不吸烟,更不敢酗酒。每次外出喝酒,都得哄我半天,做下绝不醉酒的承诺才行的。
我曾无比厌倦父亲那辈男人,厌倦他们野蛮粗鲁。
但在母亲眼里,父亲是个出色的男人,他有着庄户人特有的强健、智慧和勇气。
干农活时,父亲会不时低声呵斥母亲,嫌她干活不够好,把母亲支使回家自己干。父亲老了,倔强劲还在,我见过年轻的父亲是如何轻松地把喷雾机那般轻松地背到肩上,不用母亲帮手。我也见过年老的父亲如何痛苦地背上喷雾机,从地上艰难地爬起来,还不让母亲搭手。
父亲知道母亲对有些农药过敏,但却把那明明是关怀的话说得刻薄难听。
母亲生病住院,父亲把姐弟们哄走。
“该干嘛干嘛去,一帮人在这里杵着,嘛也搭不上手。”
父亲就这样亲自陪着母亲,十几天,父亲体重足足轻了6斤,也絮絮叨叨埋怨了母亲一大通,却没耽误孩子们一天班。
生于五十年代的父辈们,生命的强悍仿佛是锻造的,1960年自然灾害的时候,父亲才8岁,一眼便可看到透明的肚皮、肠胃里蠕动的菜叶,就靠着那口空旷的老井奄奄一息却还坚强地活了过来。父亲18岁的时候,会把200多斤粮食轻松扛到肩头,步行几里从不换肩。寒冬腊月,父辈们硬是破冰卧雪,挖河打堤。为了生计,父亲做过小买卖,牵着牲口一走就是整整一晚上。
那辈人被三年自然灾害和动荡的历史岁月洗礼过、锤炼过,似乎更是打造出了一副铁石心肠。
母亲没溺爱过我们,姐妹们所有的农活都干过,算算上了十几年的学,无论刮风下雨,他们没来接送过我一次。他们也从未疼惜过自己,大学的时候,母亲做过一次大手术,但她却不让姐弟们给我说。
那辈人的确老了,那硬扎扎的内心也变得软了。
当我训斥儿子的时候,母亲会站出来护着了。可是小时候,我们姐弟几个没少挨她的巴掌。父亲爱看战争片,会霸道地占着频道,儿子爱看动画片,却可以更霸道地从姥爷手里抢过遥控器,把那频道换来换去。
生于五十年代的一代人老了,但他们还是会骄傲地在儿女面前昂起头来,从未想过在儿女们面前服软,他们依旧拖着疲惫的身躯日夜耕作,在他们一生中,改天换地的事儿经历得多了,他们在剧烈的变化中顽强地适应着角色。
父亲依然固执地只看战争片,只会哼几句现代京剧的唱腔,没有种花养草、琴棋书画等文雅一点的爱好,他不爱逛街,不喜吃穿。如今老了,他的爱好除了庄稼活,便是抽烟喝酒,而后慵懒地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打瞌睡。
当我站到山西省郭亮村外的王莽山挂壁公路上,瞻仰这被称为“世界第九奇迹”的天路时,我总在为一种精神感动着,这种彪悍至极的景致,该是出自一群充满血性果敢的汉子之手,他们饿着肚子,破衣烂衫,筚路蓝缕,却有改天换地的决心,此种豪情怕是今之男儿所难企及的。
我还是会厌倦父辈们对妇女的轻视,但我却也渐渐懂得了一个时代男人所该肩负的责任,这或许是生于尔侬我侬时代的我们无法揣摩的了。
老父亲还会每餐前斟上一杯古贝春酒,依旧会醉醺醺地摇晃着回家,母亲依旧会看其脸色嗔怪几句,把一杯热茶递到他的手里。
“哎,你说我是不是真老了,咋一沾酒就迷糊呢?这酒呀,得少喝了!”
母亲还是不会阻拦父亲去喝酒,因为他们风雨患难的几十年,她比我们更懂父亲。
生于五十年代的这代人啊,他们像极了这醇香馥郁的古贝春酒,需要你慢慢品它,品它经岁月历练所沉积的风韵,品它情不外露深藏于心的热情,品它强悍霸道的执著,还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