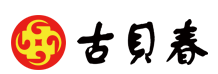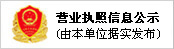我家三代河酒情
新闻分类:墨香酒韵 来源:武城县作协副主席 时云山 发布日期:2024-10-08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麦花飘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离河三里耿时潘。
解放前,我家是村里穷出名的贫雇农,房仅三间,地无一垄。为了一家七口的生计,爷爷只好白天串村要饭,夜晚到运河逮鱼,卖点零钱补贴家用。运河夜逮鱼,使爷爷与大运河结下了不解之缘。
运河逮鱼有多种方法。河边有屋,家中有船,以打鱼为生的渔家,昼撒网,夜下钩,渔具全,获鱼多。而运河岸边多数的穷苦人家,无船无钩,只有自家刮弄些竹卡子,夜里到河中卡鱼。下卡子逮鱼需要夜间看守,否则,遇有贼人会连卡带鱼偷个干净。爷爷夜晚去运河下卡子,都是傍晚时分背个荆筐,内放几挂卡子,腋下夹条棉被直奔河边。下完卡子,抽袋旱烟,一条棉被半铺半盖,就在河边沙地上宿寝;一年四季倒有二百多天夜宿河滩。别看下卡子逮鱼逮的全是二三斤的小鱼,小鱼自有小鱼的好处,做着好吃,赶集好卖。
运河夜逮鱼,需要技术,也需要胆量。听爷爷讲过,邻村有个名叫怀鞠的后生,三十多岁,在河滩上夜里看卡子时遇一红衣女鬼,吓得半夜狂奔回家,一头裁倒炕上,口吐绿水,半月身亡。后来有人证实,说他夜里以看卡子为名,常潜村入户偷盗东西,不知撞上了什么鬼怪事儿竟吓破了苦胆,也算报应。我爷爷及耿时潘村邻十几人,常年在夜里逮鱼补贴家用,几十年夜宿河滩从未遇到过怪异之事。老人在世时常说:“再凶的地方也不害好人。好人到哪里都会平安。”
运河滩湿气重,河道里风硬钻骨,下卡子逮鱼的爷爷就又与酒结缘,常常腰间挂个葫芦,里面装盛些瓜干烧酒,夜宿河滩时喝两口御寒。那时,武城运河滩上盛行地产的白酒,县城南门外“王家酒坊” 酿造的“小米香”是爷爷的最爱。艰难的日子,劳累的庄活,一家的生计,穷人的无奈,运河滩上的爷爷品出的全是生活的苦涩味道。
父亲常说起他在甲马营码头上扛脚的事儿。大概五十年代末,父亲不足二十岁,身体强壮,就与几个村内小伙儿一起去甲马营码头上装船卸船。扛脚的接包需要一个关键动作——钻肩儿,将身肩适时地钻到发起的货包之下,然后扛包下船,沉步翻堤,上垛扔包。这个动作要求技术高,不但需身强力大,而且关键动作要巧。钻肩儿时,早了,站在当地等包落肩,会在一砸之下伤了身腰;晚了,则头肩碰包,钻肩儿失败。扛货走翘板也有窍门,要挺胸、紧腿、扎脚,关键是不可与翘板产生共振。
如果说父亲码头扛脚还部分是为了自家生计的话,那么,他后来的走运河销农货可全是为了乡亲百姓。人民公社时代,农村人的日子确实过得艰难,生产队的粮棉收成勉强维持饿不死人,农家百姓要弄点零花钱难于上天,因为革资本主义尾巴把门路都堵死了。作为大队支部委员、生产队负责人的父亲,只好钻点政策的空子,以生产队的名义多种点瓜菜,卖下钱来给社员分点红,过个像样的年节。有一年,队里大白菜丰收,就在甲马营码头装船运往德州去卖,可谁知行情不好难以出手。父亲几人又将白菜倒运到下游的天津,一直到进入腊月门,菜卖完了才疲惫归来。大运河记录着那些年月里农民们的奋斗,记录着父亲大运河上为民谋利的轨迹。滔滔大运河,成了沿河人民谋生存、求发展的希望河。
押船行进在大运河中,一有难得的空闲,父亲总爱摸出随身携带的小酒瓶,嘴对瓶口来上二两。那时喝的多是“国营山东武城酒厂”所产白酒,家乡味道可以慰藉异客思苦。终年为生产队劳心费力,常年进州下卫运卖瓜菜,竭尽全力也难以使得乡亲们温饱,这种种无奈积存心中,再好的美酒也使父亲觉得辛酸异常。
我是1961年出生,在运河岸边的家乡生活了近二十年。记得小时候常去河里洗澡、玩耍,到圈地拔草、扒瓜,冬季跑上运河大堤捡拾老鸹窝掉下的柴禾,由此结识了运河大堤上看汛屋的河爷,甲马营渡口摆船的孙家父子,种西瓜的把式匠潘公,于是,后来在我的文学作品中就有了《守望》、《运河人家》、《千年古渡》、《瓜把式》中的那些鲜活生动的人物。我终于继承了老辈人热爱运河的基因,把家乡这条大河吸入了血液,植入了骨髓,融入了灵魂。写作大运河,歌颂大运河,不是我的职业,不是我的任务,而是我的使命,是来自于祖辈血脉遗传中的使命。
如今,我一边写着大运河的文章,一边悠闲地畅饮着运河名酒古贝春,这时品出的是新时代幸福生活的醇香甘甜,是国运家运自己命运的悠远绵长。
解放前,我家是村里穷出名的贫雇农,房仅三间,地无一垄。为了一家七口的生计,爷爷只好白天串村要饭,夜晚到运河逮鱼,卖点零钱补贴家用。运河夜逮鱼,使爷爷与大运河结下了不解之缘。
运河逮鱼有多种方法。河边有屋,家中有船,以打鱼为生的渔家,昼撒网,夜下钩,渔具全,获鱼多。而运河岸边多数的穷苦人家,无船无钩,只有自家刮弄些竹卡子,夜里到河中卡鱼。下卡子逮鱼需要夜间看守,否则,遇有贼人会连卡带鱼偷个干净。爷爷夜晚去运河下卡子,都是傍晚时分背个荆筐,内放几挂卡子,腋下夹条棉被直奔河边。下完卡子,抽袋旱烟,一条棉被半铺半盖,就在河边沙地上宿寝;一年四季倒有二百多天夜宿河滩。别看下卡子逮鱼逮的全是二三斤的小鱼,小鱼自有小鱼的好处,做着好吃,赶集好卖。
运河夜逮鱼,需要技术,也需要胆量。听爷爷讲过,邻村有个名叫怀鞠的后生,三十多岁,在河滩上夜里看卡子时遇一红衣女鬼,吓得半夜狂奔回家,一头裁倒炕上,口吐绿水,半月身亡。后来有人证实,说他夜里以看卡子为名,常潜村入户偷盗东西,不知撞上了什么鬼怪事儿竟吓破了苦胆,也算报应。我爷爷及耿时潘村邻十几人,常年在夜里逮鱼补贴家用,几十年夜宿河滩从未遇到过怪异之事。老人在世时常说:“再凶的地方也不害好人。好人到哪里都会平安。”
运河滩湿气重,河道里风硬钻骨,下卡子逮鱼的爷爷就又与酒结缘,常常腰间挂个葫芦,里面装盛些瓜干烧酒,夜宿河滩时喝两口御寒。那时,武城运河滩上盛行地产的白酒,县城南门外“王家酒坊” 酿造的“小米香”是爷爷的最爱。艰难的日子,劳累的庄活,一家的生计,穷人的无奈,运河滩上的爷爷品出的全是生活的苦涩味道。
父亲常说起他在甲马营码头上扛脚的事儿。大概五十年代末,父亲不足二十岁,身体强壮,就与几个村内小伙儿一起去甲马营码头上装船卸船。扛脚的接包需要一个关键动作——钻肩儿,将身肩适时地钻到发起的货包之下,然后扛包下船,沉步翻堤,上垛扔包。这个动作要求技术高,不但需身强力大,而且关键动作要巧。钻肩儿时,早了,站在当地等包落肩,会在一砸之下伤了身腰;晚了,则头肩碰包,钻肩儿失败。扛货走翘板也有窍门,要挺胸、紧腿、扎脚,关键是不可与翘板产生共振。
如果说父亲码头扛脚还部分是为了自家生计的话,那么,他后来的走运河销农货可全是为了乡亲百姓。人民公社时代,农村人的日子确实过得艰难,生产队的粮棉收成勉强维持饿不死人,农家百姓要弄点零花钱难于上天,因为革资本主义尾巴把门路都堵死了。作为大队支部委员、生产队负责人的父亲,只好钻点政策的空子,以生产队的名义多种点瓜菜,卖下钱来给社员分点红,过个像样的年节。有一年,队里大白菜丰收,就在甲马营码头装船运往德州去卖,可谁知行情不好难以出手。父亲几人又将白菜倒运到下游的天津,一直到进入腊月门,菜卖完了才疲惫归来。大运河记录着那些年月里农民们的奋斗,记录着父亲大运河上为民谋利的轨迹。滔滔大运河,成了沿河人民谋生存、求发展的希望河。
押船行进在大运河中,一有难得的空闲,父亲总爱摸出随身携带的小酒瓶,嘴对瓶口来上二两。那时喝的多是“国营山东武城酒厂”所产白酒,家乡味道可以慰藉异客思苦。终年为生产队劳心费力,常年进州下卫运卖瓜菜,竭尽全力也难以使得乡亲们温饱,这种种无奈积存心中,再好的美酒也使父亲觉得辛酸异常。
我是1961年出生,在运河岸边的家乡生活了近二十年。记得小时候常去河里洗澡、玩耍,到圈地拔草、扒瓜,冬季跑上运河大堤捡拾老鸹窝掉下的柴禾,由此结识了运河大堤上看汛屋的河爷,甲马营渡口摆船的孙家父子,种西瓜的把式匠潘公,于是,后来在我的文学作品中就有了《守望》、《运河人家》、《千年古渡》、《瓜把式》中的那些鲜活生动的人物。我终于继承了老辈人热爱运河的基因,把家乡这条大河吸入了血液,植入了骨髓,融入了灵魂。写作大运河,歌颂大运河,不是我的职业,不是我的任务,而是我的使命,是来自于祖辈血脉遗传中的使命。
如今,我一边写着大运河的文章,一边悠闲地畅饮着运河名酒古贝春,这时品出的是新时代幸福生活的醇香甘甜,是国运家运自己命运的悠远绵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