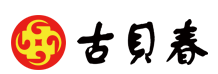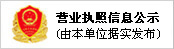遗失的美好
新闻分类:墨香酒韵 来源:古贝春报编辑部 发布日期:2014-01-02
我还是喜欢一些有年代的东西,为的是能从其身上感受一种震撼心灵的沧桑和厚重,仿佛只需轻轻抚摸它们就能扯出长长的历史来。它们把那如水般的光阴一滴一滴地吸纳、浸渍,最后完整地渗入、封存。日子去了,难复来,能用来咂摸过往岁月的,唯有这些东西了。
置身故乡大地,最能让我内心深沉的还是那条运河,站在新桥上远远遥望老桥,我所能回忆的极点是童年初次踏上这桥时的惊诧,但内心所能及的却并不是这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老桥所能承载的。尽管这运河还有一脉细流委蛇地走近又走远,早已不复当年河水满槽的浩淼与阜盛,但恰恰因还有细细的水流,这运河便还未死,依然会沉淀岁月,积淀历史。不管经历多少年,拂去这运河的厚厚泥沙,在最初的河床上定还存留着一千多年前河工滴落的汗珠和残留的脚印,泥沙中还包裹着千年前反隋义士的忠骨和铁戟,运河能挺住,便是因为这运河儿女比铁还硬的脊梁,比丝还柔软的隐忍。只要这运河还活着,便能就着这秋风凄雨,吼几嗓子豪情的运河船调儿,仰视两岸躬身向前的纤夫;只要这运河硬扎扎地立着,便能极目这衰草连天,从这涓涓的溪流里俯瞰历史的风狂雨落;只要这运河还存在着,在这现代文明的簇拥中,就依稀还能搜索出运河明珠曾有的繁荣;只要这运河还颤微微的站立着,便定然还会有远离故土的武城游子面对古运河悲情地喊出:“大运河呀,我的亲娘!”
古贝春酒的酿造工艺要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了,古运河哭了,就像满头白发、脸上沟壑纵横的老娘流下的一滴浊黄的眼泪。运河呀,你莫不就是运河儿女偎依在你怀抱中成长的老娘,那这古贝春酒呢,便是运河母亲喃喃向我们吟唱的儿歌!娘已老,歌未老。望眼运河,饮下古贝春酒,慰藉的是离愁,体味的是浓浓的故乡亲情。
无人不识京杭运河面,几人不知古贝春酒香浓。京杭运河、古贝春酒,母亲、儿歌,表述运河与古贝春酒的关系,用此形容怕是最为贴切不过了。我们要为后世子孙留住这千年不朽的运河,还有这已香飘千载不息的古贝酒香。跟运河相比,这古贝酒香所承载的岁月更为久远,更为触动灵魂。
追溯古贝春酒的历史,便如一缕酒香源于最为兴盛的殷商,轻轻漫溯过一个个更迭的王朝,随运河的清波北上南下,几度兴盛,几度浮沉,暖过君王梦,壮过英雄心,催过思乡泪,抚过状元情。携悠悠千载梦境,绘一幅幅色彩斑斓,千古兴衰荣辱,几度儿女情长,千年运河明月,街头巷尾百姓事儿,终都化为一杯盈盈欲滴的古贝春酒了。
古贝春酒的酿造工艺要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了,运河不会消失,古贝春酒香难绝,幸甚,快哉!但又有多少东西,其实已慢慢地消失在历史的风尘中了。
同族的一个长辈去世了,父亲一个劲儿地叹息,问其原因,父亲告诉我,咱村曾经名声在外的“架鼓曲谱”和“砸夯调儿”彻底没了。
这位长辈一生对架鼓的痴迷是别人难以想象的,三里五村的“架鼓曲谱”他都了然于心,而且自己还创造改进过不少曲谱。父亲说,当时只要他闲下来,便会把布鞋脱下,鞋底朝上,捡起两根木棍,噼噼叭叭地打击鼓点,揣摩新的鼓点。村里的架鼓队是他一手带出来的,他不为名,不图利,每年秋后一过,各村的庄户人便会敲起震天的架鼓,迎春祈福。这时的他便似着了魔,把一面大鼓往腰间一系,亲授新学习或创造的鼓点。父亲说,那时候的人窝头、咸菜,时不时还饿肚子,但活得特别有精气神儿。人们乐在其中,沉浸于此,敲出了人们的豪情、忧伤,敲出了希望、勇气和执著。如今,每当父亲看到人们敲的架鼓时,总还在感叹这鼓敲得绵软干涩,花样单一。我没见过村里的架鼓,但却真真地见过这位长辈多次到家里跟父亲提出要村里重建架鼓队的想法,父亲每次都会跟他耐心地解释很久,如今社会,人们讲求物质至上,村里要是买鼓容易,但要是找人天天敲鼓,那却难了,除非村里给敲鼓的人发钱,鉴于此,只有作罢了。当这位走路已经颤微微的长辈最后一次走出我家家门时,他无奈地留下了一声长叹:“多好的东西,就这么没了。”要是这位长辈能识得曲谱该多好,那样便可把其一生所钟爱的架鼓曲谱存留下来了,只可惜他只字不识,更别提写谱了。
“拿不了针,捉不得线”早已不再是衡量一位女性贤惠与否的标准了,如今,不能用钱买到的物件儿是少之又少,但我还是赞叹上辈女性们的心灵手巧。小时候,我见证过祖母是如何把一堆棉花变成身上衣服的全过程,更对纺车、织布机等物件儿有着那般特殊的情感。小时候,我能坐在纺线的祖母身旁,一动不动地盯着一团棉花如何吱吱扭扭的变成一个个饱满的线团,也曾那般心痒地想尝试过。祖母的教育总是传统和守旧的,一如她一生以自己有那双窄窄的“三寸金莲”为荣一样。她真真地想把纺线的工艺传授给我,为的是一个丫头嫁人后不至于招婆家人笑话。祖母告诉我,那时候,姑娘嫁到婆家之前都要给男方做双布鞋的,每到这时祖母的得意之情是溢于言表的,显然她的针线手艺是得到婆家首肯的。我记得祖母有一本厚厚的大书,里面夹的都是各式各样的纸质鞋样儿,村里的媳妇们常来找祖母借这些东西,也常会带些针线活来,请祖母指点。天气好的时候,祖母会找些布头、纸张,然后在其上面刷上浆糊,一层层的粘叠到一起,然后拿到外面去晒,这种类似纸板的东西是做鞋底不可缺少的材料。小时候,姐弟们都是穿祖母做的布鞋长大的,她做的棉鞋,既合脚又漂亮。孩子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每年鞋的尺码都会变化,但祖母却以其独有的方式,能准确地做出合脚的鞋子来。祖母曾有件铜质的“顶针儿”,仿佛一生都在其手指上戴着,那顶针儿被磨得亮亮的,仿佛诉说着像祖母一样一代代中国女性的智慧和勤劳。祖母老了,眼睛花得早已拿不得针线,枯瘦的指头也再无力气纳得鞋底了。如今,很少有人再穿手工做的布鞋,使用那些粗布做的物件了。祖母总在埋怨穿在脚上新买的鞋子不合脚,母亲告诉我:如今这三寸小脚的鞋子怕是很难有人做得了了,也真真有人懒得做了。现在祖母每天会坐到炕上不断地打瞌睡,却一直不停地抚摸着手指上的“顶针儿”,或许,所有技艺在她脑子里不断地闪回,却也在慢慢地遗忘。我无不悲哀地这样想:“如今世上有三寸金莲的人还有几个?等这三寸金莲消失了,一个时代消失了,一种工艺也随之消失了。”
我们古贝春酒的酿造工艺要“申遗”了,一种难以言表的情感总在内心翻搅着,这源于殷商的国酒酿造工艺,在中国历史的浮浮沉沉、兴盛动荡中能得以延续,在创新工艺、融合众酒之长的过程中能完整地传承该是一种多大的幸运。当一尊尊酒星雕像在眼前一个个地滑过,在马绍兴与杜安民的雕像前,我伫立了许久,也沉默了许久,空气中仿佛浓浓的古贝春酒香化作古运河翻滚的浪花,在历史的深处激荡出动人的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