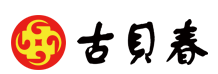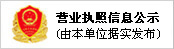我与酒
新闻分类:墨香酒韵 来源:中国作协采风团 发布日期:2012-03-02
——古贝春集团有限公司参观后杂感
此前,我已写过《我与水泥》、《我与电》、《我与罐头》、《我与橘皮的往事》等回忆类文章,若非古贝春酒厂诚邀参观,我这辈子是断不会写一篇《我与酒》的。因为,我是基本不沾酒的。在某些非饮不可的场合,只象征性地饮一小口而已。半两酒便会使我脸红,一两就绝对会使我醉倒。不论多好的酒对我都没有吸引力,滋味也都一样,苦、辣罢了。也许跟体质的基因有关——我父亲一辈子不饮酒,自然也不曾醉过。他是建筑工人,无需应酬,滴酒不沾是自己完全做得了主的。我这个他的文人儿子,则就自己完全做不了主了。所以,虽不喜欢饮酒,却下场很惨地醉过几次。只有一次,是我自己将自己灌醉的。那一年,我才上初二,十五六岁。算来,应是1965年,“文革”前一年。
那一年,我父亲已随三线建设大军去到了四川,而哥哥已经患精神病一年多了,终日将母亲和我以及两个弟弟一个妹妹折磨得无处逃避,生不如死。
十五六岁的我,不论对于个人的将来还是家庭的将来,都是看不到一线亮色的。而且,家中粮食还不够吃。那是在冬季,我这个“晋升”为长子的二儿子,从母亲手中接过她向邻居家借的购粮证,在从粮店买了半袋子高粱米背着往家里走的途中,鬼使神差地,居然绕往杂货店,用剩下的钱买了一瓶白酒。当年全中国哪儿哪儿都缺粮,许许多多的中国人还在挨饿着,所谓粮食酒,几乎全是用各地粮库里发霉了的粮食酿造的,无疑是劣质的。劣质的平时也买不到,要凭票买的。酒票平时也不发,春节时才发,反正当年的哈尔滨是这样。也不家家户户都发给,发前街道干部是要调查了解的——家中没有饮酒的人,也不发给。而酒票,是可以当作人情相送的。我家除了母亲都是孩子,为了获得酒票送人,母亲曾将一个捡来的酒瓶子刷洗干净,摆在家中明面处,以证明我家也有她这样一个喝酒的母亲的。母亲与父亲不同,她是喜欢小饮的,并且有二三两的酒量。母亲心中的愁苦比我心中的愁苦更大,我想她有时候肯定是想借酒消愁的。但,家中虽有过酒票,母亲却从未买过酒,更没饮过,一向送人情了。父亲每月只能寄回家四十元钱,长子还患着精神病;即使在当年,我家的生活水平也在哈尔滨市的贫困线以下,母亲她就是再愁,又怎么会舍得钱买酒呢?不知何故,一张酒票夹在买粮的钱卷中。那是正月十五过去多日了,再不用掉便作废了。给人应在春节以前给,十五以后给,连份人情也打折扣了——这是我擅自决定用买粮剩下的钱买瓶酒的原因,即使绕道也绕不了几十步远。杂货铺里卖酒的女人,对于我这个少年背着半袋子粮食买酒并未多么得奇怪,在那年头,过期作废了一张酒票是极令人惋惜的。
当我离开杂货铺,当一瓶白酒拿在我手里,我倏忽产生了一醉方休的念头,甚至可以说那是种希望一醉而死的念头。穷愁生活中长大的少男少女,包括青年男女,大抵是不太拿自己的命怎样当成一回事的。我看看瓶子里像水一样透明的白色液体,心想如果能通过喝它而死,实在不失为一种简单容易的死法。我想死还有一个原因,便是基于对母亲的强烈不满。母亲的全部爱心,似乎都倾注在哥哥身上了。家中除了买粮的钱,也几乎全用来为哥哥治病了。我觉得,在母亲的心目中,我和弟弟妹妹们似乎不重要了。我的念头里,不无以死表达抗议的成份。于是我咬开瓶盖,边走边咕嘟咕嘟一口接一口喝起来。那天很冷,酒很凉。咽下去后,除了嗓子、食道和胃都在发烧,倒也没什么其它特别难受的感觉。然而我没能把粮食背回家里,一头晕倒在半路了,高粱米撒了一地……
我不知自己怎么回到家里的。
迷迷糊糊的情况之下,听到母亲在严厉地问:“你为什么要这样?”
我说我不想活了,想死。
接着我就吐开了。再接着听到弟弟妹妹们全哭了。我勉强睁眼看时,见母亲也在流着泪,仰着脸喝那瓶酒,而且是咕嘟咕嘟不停地喝!我慌了,爬起来抱住母亲夺下了那瓶酒。
母亲哭着说:“你对妈很重要!你们都对妈很重要!谁小小年龄想死,就等于是让妈先死!妈是舍不得撇下你们先死的,那就不是一个好妈了……。”
我也只不过喝下去二两左右白酒,却人事不醒地昏睡至第二天中午。
……
我下乡后又醉过几次。虽然领教了酒的厉害,虽然明知醉后的滋味有多难受,但为了使别人高兴,也便只有豁出去地使自己醉倒。比如过春节时,我是班长,全班战士轮番向班长敬酒,那是没法不喝的。一口接一口,几口后,自然就醉了。比如从连队调到团里,关系亲密的知青伙伴为我饯行,也只有以醉答谢。被推荐上大学了,更多的人聚在一起依依惜别,也只有一醉方休。每醉一次,都使我增加对酒的恐惧。
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以后,有次我探家,因为酒,与四弟吵了一架,也使母亲大不开心。那是在夏季,母亲住四弟家,我在宾馆住下后,由几名接我的中学同学陪伴着前往四弟家。四弟家极小,正修火墙。火墙拆了一半,暴露着内壁黑漆漆的烟油,满地砖块和泥土。而就在火墙的前边,支起了不小的一张圆桌。那桌子一支,屋里就不剩多大空间了。桌上,摆满了大盘小盘,是四弟亲自下厨炒的菜。桌旁地上摆一箱啤酒,母亲端坐桌旁,期待着为我这个成了作家的儿子接风。屈指算来,我与母亲与四弟,又二三年没见了。可我一进了屋,脸色顿时难看起来。在我,是不解,因不解而生气。明明屋子很小,明明还在修火墙,这是干什么呢?我又不是什么稀客,而是哥,而是儿子,接的什么风呢?我认为,纯粹是四弟想喝酒了,以为我接风当借口。我并没冤枉四弟,当年的他,确实几天没喝酒就想酒喝。但四弟振振有词——他说二哥你二三年没探家了,又不是一个人来,就要到中午了,我不准备饭像话吗?虽然你不喝酒,你几名好同学是喝酒的啊!有饭没酒,对爱喝酒的人能算尽到心意了吗?再说,妈妈是喜欢热闹的人。你回来了,你同学也来,正好是个热闹热闹的机会,你一进门就激头掰脸的,你对吗你?!……
以后回想起来,我意识到自己是不对的,太不对了!但当时,我情绪失控了,言词激烈地训斥了四弟一通之后,也没跟母亲说几句话,转身便走。因为在我这方面,对待客人的诚意,并不体现于一桌酒饭,而是起码应将家收拾得整洁一些。正修火墙,不备酒饭来人也不会挑理的呀。何况来人都是我最好的同学,一人一杯清茶不是也行吗?如果我高高兴兴坐下了,你四弟陪着我的几名好同学喝起来了,没两三个小时能罢休吗?那么我这不喜欢喝酒的哥呢?也干坐着奉陪两三个小时不成?我还要参加邀请活动,也没那闲工夫啊!至于快到吃饭的时间了,那是预备大喝一顿的借口嘛!附近就有不少小饭店,连母亲也都去吃,一个小时从从容容地吃完了,岂不省事?
我训四弟时,母亲默默望着我,始终一言未发。等我回到宾馆冷静下来,意识到自己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当着同学的面大扫母亲的兴,后悔极了。
两年后我将母亲接到北京同住,心里仍记着欠了母亲一顿酒。我知道能饮二三两酒的母亲,一直希望有某种机会由我这个儿子陪她小饮一番。即使我自己不饮,但向她老人家敬敬酒,也是她的一大愉快啊!
某日,我的知青战友张富俭夫妇驾车前来我家,接我去参加一个小范围的聚会,他说他特意带了一瓶茅台。富俭当年是红旗杂志发行处处长,他爱人是体育出版社的财会处长。参加聚会的另外几人,也都是我们的兵团战友。
我问母亲想不想喝茅台?
母亲说当然想喝。
富俭夫妇便极力主张也带上母亲。
我问母亲的本是一句玩笑话,见母亲回答得认真,犹豫一下,同意了。
那天极热。进入饭店包间,里边空调开得极冷。包括母亲在内的别人们都没什么不适的感觉,我自己却已觉得冷沁肺脾了。但我想,总算有机会当众敬母亲一杯酒了,挺高兴。第一轮酒是大家为相聚而饮的。一杯,不,是一盅酒饮下,也就是三钱的小盅吧,我胃里居然顿时地倒海翻江起来。当然不是茅台酒不好,也不是假茅台的缘故(别人都说肯定是真的),而是由于一热一冷,使我的胃处于痉挛状态了。紧接着我离座大吐,将小小单间的四个角落全吐遍了……
我难以坚持下去,富俭只得开车将我和母亲送回家里。我并没向母亲敬成一盅酒。因为我不饮酒,心情好时喜欢小饮一两盅的母亲,在与我同住的三年里,连个酒字都没再说起过。
我这一生里,连盅酒都没向母亲敬过,遂成我的一大憾事。
参观古贝春酒厂时,我与酒的一些回忆,不禁地浮上心头。
古贝春酒厂的资料显示——这家1952年春由山东武城京杭运河东岸老城镇几家民间酒作坊业主集结成为的酒厂,其坎坎坷坷的发展过程中,也自有其憾事。
比如农业“跨长江,越黄河”、“放卫星”的年代,“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它要顺利发展壮大是完全不可能的。
比如“文革”年代,它虽酿出过口碑不错的“高粱大曲”,但要保住品牌,可持续地发展也是不可能的。
它的发展壮大,几乎注定了只能从“文革”结束后,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开始。
这就好比在中国凭票才能买到酒的年代,酒之对于许许多多生活贫困的百姓,借以浇愁的时候多,擎以祝贺的时候少。即使在喜庆之日,说着喜庆的话,饮着祝祝贺贺的酒,心底里大抵也是埋藏着忧的。
而现在,生活特贫困的人家终究是少了,饮酒大抵是助兴的愉快事了——这是中国酒业总体上兴盛发达的前提。
祝“古贝春”成为一切中国人助兴的美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