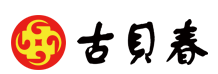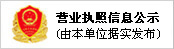迎新鞭炮过年酒
新闻分类:墨香酒韵 来源:济南市长清区国税局 发布日期:2013-03-02
古人过年,三样东西必不可少:鞭炮,春联,酒。
一到除夕,在一阵阵脆响的爆竹声中,人们用新门联换下旧桃符,心中充满了除旧迎新的喜悦。春风送暖的大年节,初升的红日照亮了千家万户,大家高举酒杯,相互祝福: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
咱们的祖先正是这样过年的。有王安石的《元日》为证:“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爆竹就是鞭炮,桃符即为春联,而屠苏则是美酒。除了贴门联,放爆竹,每人还要饮一杯屠苏酒,以期避防瘟疫,祛病强身。多温馨优雅的节日气氛,多祥瑞和谐的社会图景呀!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对炎黄子孙的影响根深蒂固。头几年,据说为了防止空气污染,城市禁放鞭炮。这可苦了城里人,一到过年,总会有一拨拨车队,从城里跑到乡下。人们顶风冒寒,碾冰踏雪,在田头,在河滩,在农家场院,点燃一挂挂鞭炮。有些无缘享受这种野趣的市民,宁肯冒着被处罚的风险,也要偷偷燃放一挂鞭。这是怎样的一种情愫呢!传统不易废,民意不可违呀。禁放效果不行,政府只好取消禁令,让人们在中华民族特有的大节下,集中释放对生活的热爱,尽情表达对未来的祈愿。
我总忘不了童年时赶“花花集”的情景。每年腊月的最后俩集,乡下人称之为“花花集”。集上货物琳琅满目,人流熙熙攘攘。从年头忙到年尾的平民百姓,都要趁着这两个集,把年货置办齐全哩。不买年货的闲人,也要来集上东游西逛,掺个热闹呢。
花花集上,最火爆的去处是鞭炮市,的确是人山人海,人声鼎沸。卖鞭炮的外地人,一簇一伙的,带着特批的介绍信,风尘仆仆,风餐露宿,走南闯北赶年集。每到一个集市上,他们支起桌子,伸出挂着鞭炮的长竹竿,可着嗓门比着吆喝:“一分钱一分货,十分钱买不错,都来买哟!”“老少爷们儿闪一闪啦,瘸子下山——又点咧!”
一阵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响过,围观的人们蜂拥而上,有的递上钱去,购买几挂;有的钻进人缝里,捡拾掉在地上没响的“臭鞭”,掰开倒出药面,再点燃“呲花儿”。
除夕夜,老乡们要在昏黄的煤油灯下,拉呱守夜。到了子夜,家家“抢时辰”放鞭炮,以图争个好彩头。初一清早串门拜年时,还要议论一番:“今年不赖哩,东街响了西街放,爆仗一宿没住点儿呢!”
自从有了电视,尤其是有了电脑,鞭炮的分量便打了折扣,连小孩子都痴迷于网上游戏,对鞭炮失去了兴趣。今年除夕之夜,鞭炮只在零点前后响过一阵,很快就悄无声息了。
一直盛行不衰的,除了必不可少的饺子,就是过年酒了。过年本来就是喝酒的日子,即使在过“革命化春节”的年代,美酒依然香飘神州。改革开放前,一般人家的过年酒是不敢放开喝的。因为酒少,国家不会敞开供应,老百姓的钱也少,想多喝也买不起。年后走亲访友,主家会很重意地摆出两瓶酒。怎么喝?一盅子倒成俩,两盅子匀成仨,划拳压指猜火柴棒,谁输了谁喝,一桌子七八个人,两瓶酒喝完就散席。酒少有酒少的好处,东倒西歪的醉汉就不多见。
后来酒多起来,洋相百出的醉汉也多了:把自行车骑进沟里,将酒瓶子摔碎在马路上,醉卧街头不省人事……有个经典的醉酒故事:一位新女婿年初二走丈人家,老丈人开明,亲自陪女婿喝酒。酒过三巡,爷儿俩划开了拳。女婿喝得大脑不够使,开口即喊:“哥俩好啊!”老丈人爽朗一笑:“好,喝酒就得有个气氛,咱就兄弟俩相称。”结果,俩人都喝高了。闺女嫌丢人,拽起女婿趔趔趄趄走了。老丈人酒劲儿上来,吐了满身,无力擦洗,倒头就睡。家里养了一条狗,很通人气,翘首咂舌,为老汉舔舐秽物。老汉睡得迷迷糊糊,觉到有条温软的东西在嘴边蹭来蹭去,连连摇头:“嗯哼,俺不吃粉皮!”狗吞食完秽物,也醉睡在老汉身边。老汉被酒精烧作得口干舌燥,一伸手摸到狗身上,赶忙推搡:“我都热成这样了,怎么还给我盖皮袄呀!”呵呵,有些夸张了,但翁婿同醉者确有其人。
现在生活好了,酒局愈来愈多,酒的档次也高了。只要不开车,谁都可以敞开肚皮喝。腊月二十三那天,朋友约我一起过“小年”,喝的是38度古贝春百年老窖。6个喝白酒的人,人均喝了一斤。古贝春酒好不上头,朋友们除了显得有些亢奋,没有一人吐酒出洋相。最后一杯“终下酒”,大家红光满面,齐喊一声:“百年老窖,长寿百年!”统统喝了个底朝天,而后心满意足地分别“打的”回家了。
关于贴春联,广大农村依然保留着这一习俗,显得红火喜庆;在城市,却大都变成了正贴或倒贴的福字。
在全球大融合的背景下,传统的东西已经越来越稀少了。我们难以想象,如果有一天,鞭炮、春联与酒被完全丢弃,还算过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