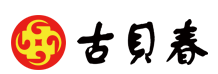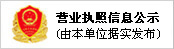俭
新闻分类:墨香酒韵 来源:古贝春报编辑部 发布日期:2013-03-31
在咱武城方言里形容某些人生活节俭会这样说:“人家‘杠细’(谐音)唻!”对于那些生活奢侈无度的会这样说:“人家‘手杠大’唻!”在我的老家,对于这两种略显极端的生活方式,人们对前一种人的生活方式更多是认可的,勤俭是老辈人所推崇的,对于那些勤俭持家、会过日子的人,村里人也是极为崇敬的。
丈夫认为是他们家老少辈儿的节俭,才促成了今天还算殷实的家境,但我却觉得,正是家境的贫困才促使一家人不得不选择节俭。
我跟丈夫是同龄人,却从出生就注定了迥异的命运。同为多姐妹的家庭,丈夫是在一家人盼望儿子的时候出生的“香饽饽”,我却是在一家人盼儿子的时候,成为继续让家庭失望的“多头儿”。在丈夫的本家长辈那里,几乎每家都有他小时候的一张照片,据说那都是已过世的爷爷奶奶炫耀般地送给别人的,在那个照相何等奢侈的年代,爷爷奶奶能做出如此奢侈的举动,足见丈夫这地位何等显贵。而我呢,在父母辗转几次把我送人未果后,算是“勉强”留下了我,当他们终于盼来梦寐以求的儿子时,超生罚款让本就贫困的家庭变得一贫如洗。在我的童年记忆里,除了姐弟间相互融洽的快乐外,剩下的便是酸酸涩涩的味道了。
已故的赵丽蓉老师曾跟李文启老师演出过这样一段小品,源头是孙子在除夕夜带回来一个玉米面窝头,并把其当作美味而腻烦吃饺子。赵老师为了教育孙子,像是煽情般地说了这样一段话:那时候家里条件差,一年到头都吃窝头儿,也就过年能吃顿饺子,有年除夕,该吃饺子的时候,因家里穷没面粉,三十晚上摆到桌上一筐窝头。现在一提这窝头儿,我的泪就……小品中,赵老师没哭出来,但我却能体味她想表达的感情。有一次,婆婆从老家回来,带回几个窝头儿,丈夫吃得津津有味,还直夸窝头儿的香甜。我一口没吃,甚至从第一眼看到它就那般厌恶它,因为触景生情,它能那般轻易地让我想起全家过得那段举步维艰的日子。丈夫说:“在我的记忆里,全家人从未把窝头儿当成过主食,偶尔做上一顿,只算是换换花样儿,解馋而已。小时候,我还曾带着弟弟到别人家的锅台上偷吃过人家的窝头儿。”总而言之,这窝头儿在丈夫的心灵里并不存在任何意义,有的也只是他对小时候调皮捣蛋的忏悔罢了。但我呢,在八零年出生的孩子们都知道,凡是超生的孩子,村里起初是不分给田地的。我能理解当时父母的心情和苦衷,对于姐弟打骂是一种情绪上愤懑地宣泄,一家七口人,老的老,小的小,人多田少,在那个国家已然号召生产四个现代化,全面奔小康的年代,全家还在温饱的边缘上苦苦挣扎。说实话,相比于上个年代挨饿的人来说,我们算是幸运的了。我没挨过饿,但伴随我童年成长的是那被同年代出生的丈夫认为是稀罕之物的窝头儿。我脑海中总会时刻闪现出那场景,在老家那条方桌上,在充斥着柴草烟味儿和新蒸窝头儿味儿的屋里面,在那个还时常限电停电点燃蜡烛的灯光下,全家挤在一起,吃的就是这窝头儿。我能感觉到玉米面儿那粗粗的碴子从食道里艰难地穿过。饭桌上的气氛沉闷无比,不是母亲训斥哪个孩子的不是,就是父母为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无休止地争吵。我时常从梦中惊醒,都说胃液是酸的,但我却感觉到一股热辣辣的液体从胃里倒上来,烧得嗓子眼火燎燎的,趴到炕沿儿上,任胃液从嘴和鼻子里流出来,我听着父母此起彼伏的鼾声,缩回被子里泪流满面。不是别人日子过得好,是我们家太穷了,我总怕别人问我吃的什么饭?从那时,强烈的自尊让我恨不得把窝头儿这个字眼儿永久地剔除,因为这窝头儿味道所承载的苦涩不是一言半语所能描述的。全家的节俭,那是根本无需提倡和发动的,贫困让节俭变得理所当然。
我不吃窝头儿,几乎不吃一根咸菜,更不喜欢吃剩菜剩饭。我会把吃不完的包子放到发霉,把剩菜剩饭倒掉,这样看起来算是奢侈的举动或许放到我的身上像是矛盾。丈夫说我是在报复,对过往贫穷不能满足的报复。有时候感觉丈夫挺馋的,会对没肉的饭菜发牢骚,但牢骚过后,无论哪种饭菜,他都会吃得津津有味,他会把剩菜吃光,甚至把汤倒进自己碗里喝掉,丈夫懂得珍惜,知道倒掉挺可惜的。
丈夫的父母过日子都是挺节俭的人,在吃穿用度上都是精打细算。丈夫说过:他们姐弟小时候虽不至于像我吃窝头儿咸菜长大,但也是吃简简单单算不上奢侈的饭菜,也会眼巴巴地看着别家孩子吃着油条而直流口水,也会为能吃上一顿肉而无比漫长地期盼。公公婆婆对生活的态度很明确,用得着的宁可奢侈,用不着的一分钱也不多花。
上小学的时候,有段时间特别时兴那种能放铅芯儿的自动笔,任凭丈夫磨破嘴皮子也没能从婆婆那里要出钱来。在全村几乎都用电水泵抽水的时候,丈夫姐弟几个还在轮流用那原始的压水井抽水。直至到后来,全村都换成彩色电视机的时候,老两口还守着那14寸的黑白电视机。在村里人眼里,公公婆婆是公认的过日子“细”。公公在一九八九年的时候买了村里的第一台喷雾18机,一下把全家十几亩地全种上了棉花,结果连续几年棉花价格飙升。一九九二年,拖拉机绝对算得上是奢侈品,但家里却已经有了这物件儿。总之,在公公婆婆看似精打细算的生活方式中,对用得着的物品的奢侈,对无用物品的节俭的风格也深深地影响着丈夫姐弟们,能供完丈夫上完大学,能让哥俩儿在县城都有房子住,公公婆婆完成了一个只靠种田的普通农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有时候感觉丈夫挺抠门的,凡是与花钱有关的习惯他几乎不沾,他不吸烟也不喝酒,一帮穷朋友也像约好般不互请吃喝,他对衣服有挑剔,却从不嫌衣服破旧。他爱玩网络游戏,被续费的小角色打得丢盔弃甲而不舍得续费一分钱,我告诉他,若人人像你,中国网游得破产,丈夫对此只是一乐。
我跟丈夫结婚初期经历过生活艰难,在最困难的时候,连工资折里的五十块钱都去柜台提取过。但我们乐观对待生活艰难,为过日子精打细算着。丈夫在花钱的哲学上跟其父母如出一辙,只要他认为有用的,花多少钱他都舍得。在单位或许穿得不是最好的,却像是很早就有笔记本电脑的,当别人还在认为空调是奢侈品的时候,丈夫执意连续买了两台空调。别人都劝丈夫买辆电动车,丈夫却骑着自己叮当乱响的自行车自得其乐:“买啥电动车,我家摩托车八年了才骑了六千公里,没用。”
我跟丈夫是同龄人,却生在了不同背景的家庭。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出生的我们懂得生活的艰难,从老辈儿那得到是“过日子不易”的教诲。成长中,我得到的是对困苦生活的恐惧,对节俭的抵触。丈夫得到的是对节俭最为朴素的认知,也是一种由家庭影响的生活方式。
“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经提出就受到很多人的积极响应,人们以形式多样的方式来履行这种号召。公司也在方方面面践行着勤俭节约,比如新出台的系列管理措施,比如对办公室“长明灯”的处罚,比如对打印纸双面利用的倡议,比如要求所有员工熟悉操作新导入的“OA办公系统”,逐步实现无纸化办公。我忽然觉得,其实不摆鲜花的会场展现的是一种刚正的美。不扯条幅的欢迎仪式上,热情的笑脸和诚挚的掌声更能感染人的心灵。当在饭店把吃剩下的菜打包后,心里反倒踏实了许多。
丈夫说:“这政策对我的思想无丝毫的冲击,我一直就是这样做的。”
我有点不认可:“你玩电脑、用空调还费电呢。”
丈夫反驳我:“你还经常倒剩饭剩菜呢。”
我拿出了一个简易的秤告诉他:“以后做饭我用它称,谁吃多少饭,提前告诉我。”
丈夫笑了:“那我还得去买两把蒲扇减少空调使用率。还得把跟网络上的人PK,改为跟儿子的‘活人PK’了。”
其实,节俭并不是一种强制自己去做什么的某种行为,只是稍微注意一下的一种习惯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