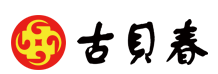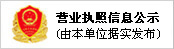酒暖人间
新闻分类:墨香酒韵 来源:山东省武城县检察院 发布日期:2013-08-31
小时候的语文教科书中,曾有鲁迅先生的《孔乙己》一文,先生笔下的孔乙己是那个年代社会底层小人物的生动写照。当时学这篇课文的时候,有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穷困潦倒的孔乙己宁可不吃饭、甚至当掉身上的衣服,也要换一杯酒喝?难道喝酒比命还重要?
曾经问过老师,老师的回答非常简单:“他就是个酒鬼。”“酒鬼”这个词在老师的语气里是带有明显贬义的,我对这个回答非常不满,因为按老师的说法,我的爷爷以及村里的许多长辈们都要排进“酒鬼”的行列。
我小时候的农村依然非常贫穷,有时甚至连基本的温饱都解决不了。村里最“繁华”的地方是代销点(乡镇这一级叫供销社),是唯一可以买到生活必需品的地方,在物质匮乏的年代,这里无疑是人们的“购物天堂”。孩子们管那里叫“小铺”,用一分钱可以买到一块糖果,因此,孩子们有事没事总往小铺跑。和孩子们一样,经常光顾小铺的是爷爷他们那些“爱喝两口的”,对于他们来说,把小铺称为“酒铺”更恰当一些。
小铺柜台的最里端,是两个大大的酒坛子,一张红纸贴在酒坛正中,上面写着大大的“酒”字。酒坛里装的就是从县酒厂(古贝春的前身)运来的散白酒,据说,那时的酒都是用地瓜干做的,但酒质很好,每次代销员揭开酒坛盖,浓浓的酒香就会弥漫满屋。在场的大人们眼睛立时放光,高声夸赞:“好酒,好酒!”馋酒的汉子会往前凑凑,使劲嗅上几口。
爷爷他们正是冲着这酒香来的。他们省吃俭用,就是为了能隔三差五弄杯酒喝,每次也就两角钱的,代销员用二两半的酒提子,把酒从酒坛里提出来,一滴不少地倒在酒碗里。爷爷端起酒,如果不多逗留,他会一仰脖把酒喝干,抹嘴走人;大多时候,爷爷喜欢坐在小铺的板凳上,一边端着酒碗细品慢啜,一边和乡邻们拉呱儿,慢慢消受这杯中之物。
爷爷去喝酒,我是每每会跟在他身边的,爷爷喝完酒,喜欢把酒碗里的最后一滴滴在我的舌尖上,看我辣得直抽冷气,爷爷会哈哈大笑,说是孩子的勇敢劲儿要从小培养,酒壮胆气,这是爷爷认了一辈子的理。尽管时间长了,我的舌尖也很喜欢接受酒的刺激,但我还是会做出很痛苦的样子,因为这样,能得到爷爷的几颗小糖。含饴弄孙,是爷爷与酒相伴的另一大乐趣。
喝酒的事,多半是发生在冬闲时节。在漫长的缺少生机的冬天,一小碗散酒,足以抵挡一天的严寒;几句舒心的话语,发散着生命的情趣。如果没有酒,真难以想象,老人们日渐缩短的人生,会失去多少乐趣,贫困的岁月里,他们又如何打发那一个个冰冷的日子?
写到这里,我似乎明白了,孔乙己为什么会对酒情有独钟。还有我的祖辈,特别是社会底层的草根一族,他们爱酒,绝不是酗酒滋事寻欢作乐,那是对酒的亵渎;也不是借酒浇愁,那同样是对酒的不敬……在他们眼里,酒就是酒,酒是神圣的,是生命里不可或缺的。在他们内心里,酒是最简单的幸福,就像冬日里暖暖的阳光,照彻世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