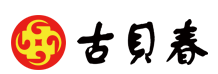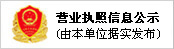古贝春里的乡愁
新闻分类:墨香酒韵 来源: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 发布日期:2014-04-01
我祖籍山东武城。祖父年轻时到安徽做木材生意,后被外曾祖父看中做了上门女婿,和祖母成婚后在安徽落户定居。祖父好喝酒,听祖母说,祖父年轻时有“不倒翁”的绰号,一到酒场上,不喝尽兴他是不会离场的,而且每次二斤酒下肚,他都能身不歪斜地离席走回家。在回家的路上,整个人始终处在似醉非醉间,酒在血液里荡漾,人在乡路上徘徊。为此,祖母虽然颇多微词,但祖父每次回家后倒头便睡,不给祖母添麻烦,倒也省心。
祖父好酒的基因遗传给了父亲,父亲年轻时酒量惊人。他1976年到青海格尔木当铁道兵,冬天为了御寒,部队在野外训练时常给士兵喝牧民们酿的青稞酒。父亲嫌青稞酒不够劲,经常和三五战友到集镇上买烈性酒。战友们喝半斤都觉上头,而父亲一喝就是二斤半,还说刚够味。于是“酒神”的绰号不胫而走。
祖父和父亲与酒相约半生,都是在50岁左右戒的酒。祖父是因为家族遗传病,医生从健康角度考虑,让他戒酒。祖父本不顾忌,但一想到父亲还未成家,叔叔们都还年少,就听从了医生的话。直到父亲和叔叔们都成家立业,他才又端起酒杯,限量饮起了自家酿的高粱酒。当年的豪情虽然不在,但适量饮酒的好习惯却保持了下来。
父亲则是在45岁那年,由于酗酒喝出了胃出血,不得已戒了视为知己的酒。戒酒后的父亲一度难以适应,常把水装在酒瓶里排遣孤寂。那一段时间,我看着父亲喝着从酒瓶里倒出的水,既心疼他的身体,又心疼他无酒为伴的落寞。
不过,祖父和父亲的好酒量却没有遗传到我身上。尽管我也好喝酒,但酒量只有三两,再多必醉。每次回山东老家,和同宗兄弟畅饮,我都是十足的看客。为此,祖父和父亲不止一次说我,咱老周家“好酒”的名声都被我败光了。
这几年,祖父和父亲因为年龄的关系,回老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了。每年春节后都是我回老家,他们是千叮咛万嘱咐,交待这交待那。临了,还不忘告诉我,从老家带瓶酒回来。我很纳闷,酒都戒了,还带酒。况且老家好东西多的是,为啥非要带酒?
今年春节,我回老家后遂了两位老人的心愿,给他们带回两瓶古贝春百年老窖。祖父和父亲喜出望外。一个劲地直咂嘴。我永远难以忘记正月初五的中午,祖父和父亲面对着两瓶百年老窖时那动容的表情。
先是父亲,一遍遍地抚摸着酒盒,拆开,又一遍遍地抚摸着酒瓶。启开,给祖父倒了一杯,又给我倒了一杯,酒香四溢。父亲抿了一口,尽管戒酒多年,但他对酒的辨识却是异常独到:“酒是故乡好,酒是故乡好,老家的酒,酒里面藏着根。古贝春的酒,浓,香。”
祖父三杯酒下肚,话匣子就打开了。说起他当年做生意时的情形,说起他当年和祖母认识的前前后后,说起这些年所受的苦、所享的福。仿佛一杯酒让他回到了昨天,也让他年轻了几十岁。他再喝时,鼻子在酒杯上闻了又闻,一行老泪不自觉地流了下来。
这一瞬间,我仿佛明白了什么。两瓶古贝春百年老窖,红色的瓷瓶,红色的包装。尽管这些年祖父背井离乡,在安徽生儿育女,但他的根却依旧在山东,在武城。“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先成泪。”一瓶家乡的酒,是用故乡的水和灵气酿造的精华。保留了故乡的气息,也保留了故乡的味道。在一瓶酒中,就能读懂人生的点点滴滴,读懂岁月的风风雨雨。
那一个中午,我陪着祖父和父亲一起喝酒,回忆往事,寻找宗谱的记忆。是啊,“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山东老家葬着祖父的父母和爷爷奶奶。那就是祖父酒中的念想和乡愁啊。也许,一杯古贝春酒,就让这一切近在眼前,停留心田。古贝春的酒,老家的酒,酒里盛着满满的乡愁,酒不醉人人自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