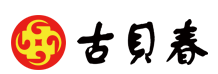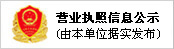春归无觅处
新闻分类:墨香酒韵 来源:古贝春报编辑部 发布日期:2014-05-04
公司园区的各种花热热闹闹地开放了,一丛丛、一簇簇的在古贝春这富有灵气的土地上开得那般恣意和随性。那白的似云朵,点缀于苍松翠柏间,恍若一汪西湖之水旁素洁圣雅的西子危坐浣纱。那红的似朝霞,如那倾国倾城的天朝贵妃,一杯酒,红晕香腮,一曲愁思,一曲离别。还有那粉的,剔透似貂蝉,那黄的,肃穆若昭君,仿佛每一朵花便可幻化出一幅最美丽的画面,这便是春天,万物蛰伏一冬所要急切迸发的盎然生机。
古贝逢春兴诗酒,酒便是浓香馥郁、万家飘香的古贝春酒,这酒应时而生,遇春而诞。那这春的诗,纵观古今,更能信手拈来,像那“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赞的是春的舒爽和惬意,像那“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感的是这春的忧郁和感伤。还记得国学大师季羡林馈赠给公司的那句“梨花带雨飞琴上,柳色和烟落酒中”吗?慨的便是我古贝春酒的诗情画意、荡气回肠和舒缓婉约。
时至谷雨,已然春末夏初,对这匆匆而过的春季,我总有一份不舍在里面。当出神地望着春雨轻轻敲打窗前绿叶,听风摇动枝叶,让那雨珠变得淅沥索啰时,却猛然把那句“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的诗句送到耳边,把那份愕然与眷恋深深地送入心底,把思绪带回到已逝的春天里。
童年的春天里,有满树挨挨挤挤的榆钱儿,有数都数不清的槐花,有随处可见鲜嫩的“姑姑提”(谐音,一种野草),有塞满鼻腔新耕的泥土芬芳,有悦耳单调的柳笛声声……。我那般轻易地就陶醉于童年春天里的点点滴滴、一草一木中了。忽然感觉一阵凉风从窗户的缝隙中溜了进来,打断了我的思绪,眼前的电脑屏幕上,一幅幅修饰好的田园风景画缓缓划过,仿佛那翠绿被涂了颜色,那红艳做了加工,生硬呆滞、了无生机。但有一幅画却吸引了我,背景是模糊的淡绿,近前是一抹柳枝的青翠,最传神的还是那只小虫,松开柳枝,展翅欲飞,在我心里,这便是春,这才是春。
童年的春天里,少不得燕子秋去春来,感慨般地罗里罗嗦地鸣叫,更难忘巷子口那声长长的吆喝声。
“小鸡儿喽吼!有卖小鸡儿的喽……”
记忆中,一听到这声音,祖母便会颠着小脚儿追出门去,可又会多次地折返回来,边走边嘟囔:“北庄的小鸡儿不好,公鸡多母鸡少。这南村的老刘头咋还没来?那小鸡儿皮实好养活,母鸡还多……”
我最喜欢被祖母拉着小手往外跑,往往没几步,开始由我拽着她跑了,这时祖母会朝我吼:“死妮子,别把我拽倒,快去喊老刘头,别让他走了!”老刘头的那竹篾笼子大大的,很有层次地固定在自行车上,远远就能听到小鸡崽儿稚嫩的叫声。我清晰地记得老刘头那时的打扮:对襟粗布褂,扎起裤腿的浆黑粗布裤子,老头鞋,头扎毛巾。老刘头的吆喝有特点,高门大嗓那种。他秋冬季走街串巷收鸡蛋,开春转暖后卖小鸡崽,人实在,童叟无欺。往往在秋冬季来收鸡蛋的时候,我会趴到地上很是费力地用自己所掌握的最好方法去计算鸡蛋的价格,从3分到5分,从5分到7分。而祖母不是,这个未上过一天学的老太太眯着眼睛,用拆零凑整的方式心算,而且每次都比我算得快。买小鸡的时候,祖母会把那些挤到一起的小鸡崽们来回拨拉几下,抓起一只仔细端详,嘴里还嘟囔:这个长大指定是个小公鸡,不能要,这个没精神儿,难养活。挑选十只小鸡崽,祖母往往会用上半天时间。老刘头也不着急,时不时地吆喝几声,慢慢地便有更多人围拢上来。算买鸡崽的钱比卖鸡蛋容易多了,祖母一般不会买超过十只,她怕养太多的鸡糟践粮食。买完后,我端着装鸡崽的纸箱在前,祖母在后面跟着,还不住地提醒我:“看着道儿,别摔了!”
这些场景,仿佛一直在眼前晃悠,祖母老了,村里仿佛再也没人费力养这小鸡崽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老刘头,却很是怀念他那悠长婉转的吆喝声。
我望着窗外的雨像一条扯不断的线,顺着窗户往下流淌,朦朦胧胧的,我看到玻璃上有只小虫慢慢地爬了上来,我赶紧打开窗户,把它拿到屋里,这家伙浑身湿漉漉的,鼻子尖上还沾着泥巴,它害怕了,奋力地张张翅膀想逃走,却因翅膀浸湿,原地不停地打着转儿,这是一只“黑老婆”虫,还有一种跟它个头儿差不多,只是颜色暗红,我们叫它“红老婆”虫。还有两种个头比它们大很多的,一种中午出现,周身金黄油亮,我们叫它“金将军”,另一种只有夜晚才出现,一身鲜红,像是古代的新郎官,我们叫它“大官郎”。
小时候一放学,孩子们扔下书包,抓个酒瓶儿,抄起小铲儿便向村西的沙土岗子进发了,小伙伴们会用小铲儿不厌其烦地把沙土翻起,寻找藏在里面的老婆虫,等到夕阳初上,天气转凉,老婆虫会从土里钻出,飞到树上,它们像是喜欢那些刚刚冒出新芽的榆树。几个男孩子会围住老榆树,叫起号子,一起踹树。憨憨的老婆虫还没来得及飞便如雨点般的噼噼剥剥落到地上,孩子们兴奋地大叫着,快速地捡拾着,欢快地大笑着,相互炫耀着自己瓶子里的战果。战果小的孩子便会唱起那首童谣:“黑老婆,红老婆,快往俺瓶儿里来两个……”夜幕降临了,村子里的灯光影绰可见,那只有春天独有的晚风悉悉索索吹到脸上,说不上的舒服,“大官郎”在矮草棵底下,仔细听,那此起彼伏的嗡嗡声响,循着声音用手去摸,往往能一下就抓到三两只。总能记起那时候的兴奋,像是捡拾遗落凡间的颗颗珍宝。
那只老婆虫还在桌上一次一次奋力张起翅膀,我却像即将失去一位老朋友般伤感,随着剧毒农药的大范围使用,这当时随处可见的童年伙伴越来越少,几近绝迹,没人在这个特定的春季里怀念它们了,因为它早已失去了人们奋力抓它的价值。我打开窗户,老婆虫终于飞起来了,逃出窗户,消失在蒙蒙的细雨中。
我看那在杯中慢慢沉下的绿茶,像极了一种难以言说的心情,在别人看似美好的意境中,我却要咀嚼一种失落,就像别人永远不愿提及童年的苦涩,我却难忘记那时的纯真和快乐。有句歌词写得好:就算生活给我无尽的苦痛折磨,我还是觉得幸福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