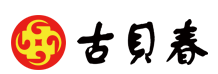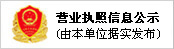家园
新闻分类:墨香酒韵 来源:古贝春报编辑部 发布日期:2012-05-05
小时候,一帮孩子疯跑一阵后便会四仰八叉地躺在青草坡上。
身下的草嫩嫩的、柔柔的,像张温馨的大床。风暖暖的、轻轻的,扑啦啦地搔动着耳鼓、拂过面颊,灌一鼻腔青草的馨香和泥土的芬芳。眯起眼睛,头顶是蓝得透亮的天空,游荡的朵朵白云轻盈舞动。
青草坡前,静卧着宁静祥和的村庄,蓝天为幕,绿树掩映红墙,炊烟袅袅,鸡犬相闻,这就是我可爱的故乡,乡亲们世代相传、繁衍生息600多年的家园。
村东,十几栋居民楼已经拔地而起。或许过不多时日,我的乡亲们便会在这宽敞明亮的楼房里开始另一段人生了。
那我的村庄呢?或也过不多时日将被轰鸣的机器夷为平地,便也把600年的历史掩入这漫漫黄土之下了。
惟留追忆……
清明节,空气中本已充满了浓浓的哀伤,望着这即将人去楼空的村庄,心里更是增添了那么多的惆怅。尽管这街道,这路边的房子多半已很破旧,尽管村子里的年轻人都出外谋生而显得那般空落,但在我眼前还总会浮现出这村庄曾有的繁华,曾有的热闹。
600多年前,祖先们应该是从西边的小路上,携妻带子,用小车推着简单的行装来到这里的,在明朝永乐皇帝践踏的土地上,在这燕王扫北而留下的白骨累累、荒芜人烟的战场上创建了这祥和的家园。
老槐树
离别于山西那株槐树,槐树便是念想,是思念的寄托。
村里曾有棵老槐树,相传为先祖们从故园带来,栽种在村子中央,后来这树长的枝繁叶茂,在地下蔓延的根系让整个村庄都长满槐树,后来那棵大槐树死了。村里陆陆续续地长出过不少大槐树,但没有一棵能像那棵老槐树那样茂盛。
在我家老宅的后面,有棵大槐树,它高高地站立在坡上,撑开大大的树冠,把个屋角遮蔽得严严实实。此树是曾祖父所栽,曾祖父40多岁就因病去世了,那时候父亲还没出生,以此推算这树少说也得有60年了。
二爷是在这老宅里走出去的,在关外闯荡了几年后慢慢混出了名堂,这树的作用瞬间便有了另外的意义。祖父当时在这屋后栽这槐树也或是考虑到偌大的后墙裸露在大街边,于风水角度来说真是有些不吉利,便想在屋后面找点东西稍稍遮挡一下。自从有了二爷的出人头地,这槐树便神秘起来,诸如这树是神木,神木遮蔽下必出人才的说法竟流传开了,祖父和父亲等老辈人更是笃信这树的神力,倍加珍惜。那年村里电路改造,这槐树茂盛的枝杈快要与电线搅在一起了,最可行的办法便是砍掉此树,没想到已年迈的祖父拄着拐棍,把在村里当电工的二哥追得满村跑。最后不得不采取了折中的办法,把影响线路的几个大枝杈锯掉了,看到光秃秃的树冠,祖父难受得好几天都没说话。
祖父美好的心愿是希望此树能庇护子孙万代加官进爵,我理解祖父的美好希冀,更宁愿相信我能考上大学是这老槐树的庇佑,但遗憾的是我祖父没能看到这一切。
二爷最后一次回家省亲时,特地让孩子们搀着他到那老槐树前看了看。秋日的老槐树,不时地飘下金黄的叶片。
“这树只是承载了你曾祖父的嘱托,他告诉我们无论多困难都得坚持。这树让我跟当年同样年轻的你祖父感觉到,你曾祖父是一直跟我们在一起的。至于别的意义,别太在意了。”
二爷的话让我第一次感觉到这槐树的温暖和亲切,明白了奋斗是远远高于一味希望命运的垂青的。
去年冬季,二爷去世了,他没有要求把尸骨带回老家安葬。在遥远的东北,二爷的灵魂定已飘回这老槐树下,细细咂摸自己曾有的苦难和永不言弃的坚持。
四叔的代销点
代销点便是超市的前身吧?说不准。
但本家四叔的这代销点却很有年头了,生产队分开单干后,四叔的父亲就干起了这营生,30多年应该有了。
村里人离不开这代销点,日常杂货都得到这里取,四叔两口子脾气好,待人谦和,又肯下力,这代销点的规模也是越来越大了。
年幼的儿子拉着我一溜小跑便到了这小超市门口。
不到四岁的儿子认识舒同先生的“古贝春”三字,或许孩子也是因为我在古贝春公司上班的缘故,耳濡目染了。
这不四叔的超市门口挂着古贝春的宣传标语,还有串串灯笼呢。
四叔一把就抱起小家伙,儿子也竟不客气地在这四姥爷的货架上拿了一堆零食。
“丫头,姊妹几个都回来了?”四婶问我。
我答应着。
我跟四婶儿有一句没一句地拉着家常,放心不下调皮的儿子。
儿子手里拿着一瓶古贝春百年老窖颠颠地朝我跑过来,四叔在后面护着他,怕他把酒给打碎。
“姥爷的酒。”我明白孩子的意思。父亲喝了半辈子古贝春酒。
“让你姥爷喝百年老窖,也就是你舍得。”四叔乐得不行。
四婶儿嗔怪四叔不该这样逗孩子。
想到拆迁后,这小店也就没有了,我不无伤感。
其实四叔已经在安置的小区里买下门市,他开玩笑说要把这小店干成百年老店。两口子构筑的美好未来,令我都无比地期待和向往。
想想人生其实就是不断编织的故事,故事的精彩与否,不在情节的曲折与否,而在于听故事者的心情。
将来,我的儿子应该会记得这四姥爷的小店,会不止一次听四姥爷给他讲他在三岁的时候就知道给姥爷买酒喝。
那便相信明天会更好吧!从小我就能嗅到古贝春淡淡的酒香,或许再过70年,这酒香在百年的历练酝酿中定会愈发地香醇。
废弃的小学
小学年岁不长,有20多年历史吧?
以前村里没有小学,学校的前身是村里为上山下乡的知青修筑的宿舍,知青们回城后,听说当过村里的仓库,后来村里上学的孩子多了,便将其稍加改造成了学校。
学校老师都是村里有点文化的青年,略微学习便当起了民办教师。
校园更是开放的场所,夏天秋天都会有不同的粮食铺满整个校园。周围村民的猪牛也会不时跑进校园一顿撒欢践踏。学校里吆喝牲口的声响和孩子们的读书声混在一起,那真是别具风味。
教室内的课桌称不上是课桌,都是用长木板搭起的长条桌,两人共用一个的长条凳。上学的时候,我跟调皮的本家侄子当过同桌,那小子恶作剧般地猛起过好几次,把我摔倒在地上。为此,老师提着他耳朵拧得他只咧嘴求饶。
如今,村里的孩子们早都去条件好的地方上学了,这教室也因缺少管理而破烂不堪。但我很是留恋这学校,留恋这里的每一位老师,在这里我得到的是知识的最初启蒙,是和外面世界的亲密接触。我的老师更是用自己并不专业的教学手段培养了我好的学习习惯,教我踏踏实实做人,他们让我了解了知识的可贵,理解了人生奋斗的价值。
校园里也有棵大槐树,每年槐花开满枝头的时候,即将毕业的学生都会在这树下毕业合影。如今槐树依旧在,槐花依旧开,但早已物是人非,人去楼空。
离安置小区不远的地方要建一个小学的,规划图中的校舍很漂亮。孩子们再也不必像我们小时候一样,冬天上课前先使劲跺跺脚取暖,不必担心凛冽的寒风随时会刮破塑料堵住的窗户,也不必夏天头顶化肥编织袋冒雨去上学……
经历苦难是不幸也是万幸,它能让人懂得珍惜来之不易的生活,懂得逆境中更需奋斗不息。
尾声
在电脑的google卫星地图上我不止一次地俯瞰过自己的家乡,我仔细搜寻村里每条街巷,每间房舍,我总难相信它会在某天从地图上消失。当儿时的我仰望蓝天的时候,总想某天我会从它头顶飞过,看全她的容貌,她的美丽,她腾起的炊烟,她滚动的麦浪,她飞舞的柳絮,但这终究成为我一生的遗憾了。
600年前,祖先们是带着心酸和苦楚来到这不毛之地的。600年后,我们再离开的时候,只是多了几分不舍,但迎接我们的必将是时代带给我们的幸福和安康。
要离别家园了,纳兰性德的那首《好事近》的词又回荡在耳边:“何路向家园,历历残山剩水。都把一春冷淡,到麦秋天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