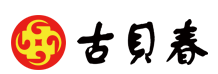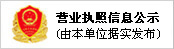麦香久远 酒香依旧
新闻分类:墨香酒韵 来源:新厂灌装车间 发布日期:2015-07-04
不知大家是否有同感,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收麦已不算大事,麦子熟了忙一阵,很快就完事。你看几亩、十几亩即便二十几亩麦田,有大型联合收割机,从收到卖,从卖到种,一站式的,省略了传统收麦子的许多环节,让广大农民从繁重的体力劳作中解脱出来,有更多时间做其他事。
现在过麦的周期是越来越短,过麦的氛围也越来越淡,之所以印象不深,是因为过麦根本用不着你,没有“感同身受”。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正上小学,父母在老城酒厂上班,一到麦收,学校放假,父母忙着上班。公路上,一夜间就铺上厚厚的“草垫”,经车反复碾压,秸秆亮闪闪、金灿灿,在正午毒辣阳光的照射下,光芒四射,刺得你睁不开眼,浓浓的麦香也随即蔓延开来……在这厚厚的秸秆上,你是摔不痛的。有一年奶奶从东北来,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奶奶,她来时正赶上过麦。有一天,爸爸骑车载她上街,车子一滑,连车带人一起摔在厚厚的麦秸秆上,这可把我们吓坏了,好不容易才把她扶起来,她却说跟沙发床一样,没事,很舒服,我们不免大笑。这时家有麦子地的同学,是没时间跟你玩耍的,他们做饭、送饭、看孩子、看麦场……小大人,忙得不亦乐乎。爸妈虽然一到过麦工作很忙,但再忙,他们还是会挤时间帮外公收麦子。早早打上一大桶散酒,天不亮骑车往外婆家赶。那时割麦子可是“纯手工”活,磨镰嚯嚯,爸妈、舅舅也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一挥而下,一片片麦杆倒地。因不经常干农活,爸妈手上很快磨起血泡,胳膊经暴晒,黑红黑红。麦熟一晌,要抢收抢种,千万别赶上雷雨大风天。那时经常听老人说,农民最大的事、最苦的事,一是盖新房,能让人掉十斤肉,再一个就是过麦,能让人脱层皮,真不假,那时过麦少则一星期多则半月,天天三更半夜起,起早贪黑干。饮食也是很节俭,一是没条件,二是没时间,主要是咸蛋、咸菜、馒头、果子、白开水。那时外公家还算“奢侈”,有外婆在家专门做饭,炒个菜,做个差样的饭菜,因为外婆身体不好,很少干农活。爸妈他们将麦子晾晒在打麦场,回家吃午饭。等外婆将一桌精心准备的饭菜上桌,我们的古贝春酒一上桌,顿时酒香四溢、饭菜飘香,大家推杯换盏,谈工作唠家常,场面温馨惬意,我虽是这场“收割大战”的旁观者,但却被深深感染着、吸引着。
九十年代中期,我不上学了,来到酒厂上班。到麦收时节,灌装车间就会加班灌装,到那时才真正了解了当年爸妈过麦时为什么那么忙。这时农民生活条件好了,过麦已不买散酒喝了,而是买瓶装成捆的古贝大曲。结婚后,婆家有地,头几年一到过麦,总和小叔子一家回老家过麦,这时已有联合收割机,但还未普及,因为大多家庭喂有牲畜,往往只收割不脱粒,麦秆用拖拉机从地里拉到麦场,抖满全场,中午饭后一天最热的时候开始翻场、轧场、起场……热得人们面红耳赤、嗓子冒烟、精疲力竭,那时才感到过麦的辛苦。我和婆婆、弟媳早早回家做饭,婆婆像过年一样,排骨、鸡鸭鱼、各种蔬菜、好酒一应俱全,酒也喝上了盒装的精品古贝春,过麦也就两三天结束。2000年后,老家牲口卖了,地也只剩二亩八分,再过麦时,联合机一收,粮贩从地头就把麦粒买走,省时省力。虽然少卖点钱,但不用来回折腾。现在过麦,老公也依然回老家,但只是看看,也依然喝着古贝春酒,不过已换成星级的,而这也不再是节令的奢侈饮品。
“麦”是年年过,但在时代的变迁中,过麦的气息不浓了,可以预测在不久的将来,大土地承包商就出现,专职种地,一部分农民将土地转租,过麦的氛围将更淡,真有一点怅然若失之感,是怀念还是留恋?说不清楚。但“有所得必有所失”,你觉得呢?
现在过麦的周期是越来越短,过麦的氛围也越来越淡,之所以印象不深,是因为过麦根本用不着你,没有“感同身受”。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正上小学,父母在老城酒厂上班,一到麦收,学校放假,父母忙着上班。公路上,一夜间就铺上厚厚的“草垫”,经车反复碾压,秸秆亮闪闪、金灿灿,在正午毒辣阳光的照射下,光芒四射,刺得你睁不开眼,浓浓的麦香也随即蔓延开来……在这厚厚的秸秆上,你是摔不痛的。有一年奶奶从东北来,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奶奶,她来时正赶上过麦。有一天,爸爸骑车载她上街,车子一滑,连车带人一起摔在厚厚的麦秸秆上,这可把我们吓坏了,好不容易才把她扶起来,她却说跟沙发床一样,没事,很舒服,我们不免大笑。这时家有麦子地的同学,是没时间跟你玩耍的,他们做饭、送饭、看孩子、看麦场……小大人,忙得不亦乐乎。爸妈虽然一到过麦工作很忙,但再忙,他们还是会挤时间帮外公收麦子。早早打上一大桶散酒,天不亮骑车往外婆家赶。那时割麦子可是“纯手工”活,磨镰嚯嚯,爸妈、舅舅也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一挥而下,一片片麦杆倒地。因不经常干农活,爸妈手上很快磨起血泡,胳膊经暴晒,黑红黑红。麦熟一晌,要抢收抢种,千万别赶上雷雨大风天。那时经常听老人说,农民最大的事、最苦的事,一是盖新房,能让人掉十斤肉,再一个就是过麦,能让人脱层皮,真不假,那时过麦少则一星期多则半月,天天三更半夜起,起早贪黑干。饮食也是很节俭,一是没条件,二是没时间,主要是咸蛋、咸菜、馒头、果子、白开水。那时外公家还算“奢侈”,有外婆在家专门做饭,炒个菜,做个差样的饭菜,因为外婆身体不好,很少干农活。爸妈他们将麦子晾晒在打麦场,回家吃午饭。等外婆将一桌精心准备的饭菜上桌,我们的古贝春酒一上桌,顿时酒香四溢、饭菜飘香,大家推杯换盏,谈工作唠家常,场面温馨惬意,我虽是这场“收割大战”的旁观者,但却被深深感染着、吸引着。
九十年代中期,我不上学了,来到酒厂上班。到麦收时节,灌装车间就会加班灌装,到那时才真正了解了当年爸妈过麦时为什么那么忙。这时农民生活条件好了,过麦已不买散酒喝了,而是买瓶装成捆的古贝大曲。结婚后,婆家有地,头几年一到过麦,总和小叔子一家回老家过麦,这时已有联合收割机,但还未普及,因为大多家庭喂有牲畜,往往只收割不脱粒,麦秆用拖拉机从地里拉到麦场,抖满全场,中午饭后一天最热的时候开始翻场、轧场、起场……热得人们面红耳赤、嗓子冒烟、精疲力竭,那时才感到过麦的辛苦。我和婆婆、弟媳早早回家做饭,婆婆像过年一样,排骨、鸡鸭鱼、各种蔬菜、好酒一应俱全,酒也喝上了盒装的精品古贝春,过麦也就两三天结束。2000年后,老家牲口卖了,地也只剩二亩八分,再过麦时,联合机一收,粮贩从地头就把麦粒买走,省时省力。虽然少卖点钱,但不用来回折腾。现在过麦,老公也依然回老家,但只是看看,也依然喝着古贝春酒,不过已换成星级的,而这也不再是节令的奢侈饮品。
“麦”是年年过,但在时代的变迁中,过麦的气息不浓了,可以预测在不久的将来,大土地承包商就出现,专职种地,一部分农民将土地转租,过麦的氛围将更淡,真有一点怅然若失之感,是怀念还是留恋?说不清楚。但“有所得必有所失”,你觉得呢?